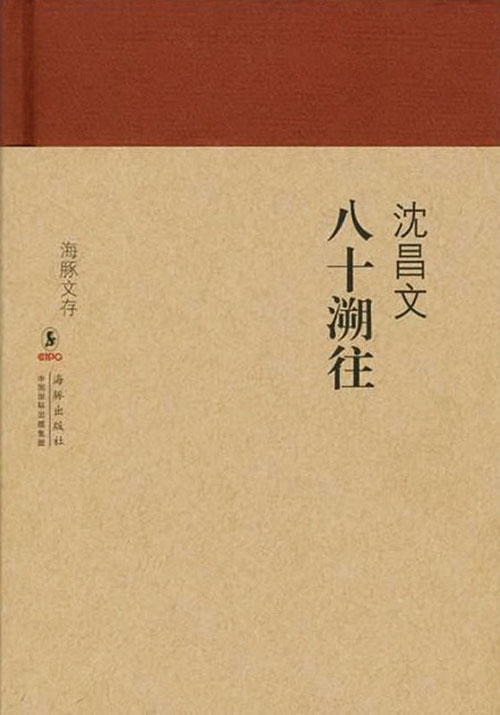我唯一的完整学历①
作者:沈昌文②
一辈子干文化工作,常同文人学士打交道。当编辑有个习惯,遇见初识的文人学士,总要打听对方是在哪里出身的。因为一知道他毕业于某校某系,凭自己的经验,大概可以揣想出他的师承和学派,然后就有话好说了(同时也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了)。要是自己熟识这个大学的学术领袖,还给他出过书,效过力,接下去更大有吹嘘的了。但是,这办法没法用在我自己身上。我除了小学,从来没在某个学校毕过业。说自己自幼失学,也对。可是,同龄人中,大概也没我上过的学校多。一九五三、一九五四年,为了向党“忠诚老实”,原原本本交代一遍自己上过的学校,当时记得已有十四五处之多。要是把小学、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,大概有二十处吧!
前面说过,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。除此之外,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,想学一些技能,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(上海人叫它们“野鸡学堂”)里瞎混,如是而已。不过就小学说,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。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,现在更名为上海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③。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?这得从头说起。